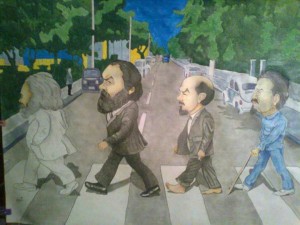近日,社会主义行动收到来自台湾读者的信件,对社会主义者民主运动的路线提出疑问。左翼分子之间同志式的交流对澄清理念、强化运动有所裨益,我们无任欢迎,因此亦公开信件内容,解释我们的立场。
台湾读者的来信(2013年11月2日)
您好,我想和您们请教。我看到了您们的一篇文章,并且长久以来对于CWI在这方面的立场,抱持疑惑。所以想来信商榷了解。
我观察到CWI在香港的活动,经常是站在支持香港和中国大陆通往“普选”的方向,并在这过程宣传要通往社会主义的纲领。
例如在:https://chinaworker.info/hhk/2013/06/02/2627/
其中你们提到:
“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站在群众身边奋斗,支持寸进的民主改革,但同时主张民主斗争必须连系至推翻中共独裁和中港两地的资本家。我们主张以真正的民主议会取代将跛脚的立法会,由16岁以上人士普选产生,议会有权力选出政府,并实施有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调高最低工资、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价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纲领去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
我想请教,这个“真正的民主议会”,如果不过是“由16岁以上人士‘普选产生’”,那么,不就代表是没有排除资产阶级对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因为并没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
我的担忧是,倘若如此,结果不就很可能会和我们在台湾经验中看到的,普选带来的形式民主化,只是让资产阶级更能够正正当当地掌握政权(透过自行参选或者金援选举)?例如中国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选国家领导人了,要不共产党官僚层继续胜选,或如同一般资产阶级国家一般,由真正的资产阶级上台。因此,我不是很能理解诉求“普选”对于革命运动真有帮助吗?(自由权利对革命运动是有帮助的,我可以理解)换言之,如果我没记错,你们的文章,有提到过要从普选迈向人民议会。但现实上,从“普选”(包含资产阶级影响下的一人一票)如何可能迈向“人民(工人)议会”呢?
我会认为,站在革命左翼的角度,逻辑较一贯的主张应当还是,直接主张“排除资产阶级势力的工人民主选举组成苏维埃,形成政权”,而非支持“普选”。
不论是中国大陆或香港民众,对于透过普选来落实政治改革、节制贪官等的期望,可以理解。但应当还是要更引入阶级观点地宣传:问题在“工人民主”,而非不分阶级的“普选”,来解决种种压迫。
这是我观看您们文章的一些些未必成熟的想法,私下寄信给您们,供您们参考、指教。
社会主义行动的回信(2013年11月5日)
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由资本家主导,通过他们的媒体、资本家政党,并利用经济力量控制选举,让工人表面上可以“发声”一下。现实上这是不民主的,但社会主义者捍卫所有民主权利 –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组织自由、罢工权,反对警察和国家打压。如果这些权利面临军事或法西斯政权的威胁,我们会倡议工人阶级战斗,保卫这些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资本家保持最后控制权,但又被迫让工人阶级公开组织、抗议、组成工会和政党、参与选举,去监督资本家的权力。在今天希腊等危经国家,欧盟官僚和银家等资本家说现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较专制的政权去解决危机(即要穷人埋单)。
在香港,议会是由资本家控制的,他们利用不民主的议会制度,确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过。因此,资本家是反对香港吋进的民主改革。民主斗争需要由基层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成功。这亦解释了香港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民运上往往与中共妥协,尤其是民主党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斗争的路上,CWI不倦的强调,资产阶级今天不再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是资产阶级的“年轻之过”),从而激化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不信任,强调运动需要以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才能成功。我们以行动说服群众,社会主义者是最坚定的民主派,同时毫不饰掩提出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之密不可分。
我们支持吋进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选权、废除功能组别,但不仅于此。我们强调需要召开新的民主议会,打破现存的立法会,除了彻底的民主诉求,包括16岁投票权、移民工投票权,亦指出新议会必须实施迫切的社会改革,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民主公营化银行及大企业等,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不错,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或过渡诉求,但我们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党派不能实行这些任务,让群众在斗争经验中学习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的必要。
关于“例如中国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选国家领导人了,要不共产党官僚层继续胜选,或如同一般资产阶级国家一般,由真正的资产阶级上台。”如果在未来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阶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权夺权,普选议会当然可以废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领导运动,即使是这种偷梁换柱的议会,社会主义者绝对应该参加,并在议会中提出彻底的社会改革诉求,迫使资产阶级摊牌,揭露妥协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应该提出“国民议会”口号,其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包括没收地主土地、中国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等,以民主口号动员工人阶级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而斯大林主义者在革命败退后,却提出即时夺权的冒险主义口号,掩饰革命的失败。在理论上,这是脱离群众意识;在实践上,则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广州苏维埃受军阀镇压。
在“工农胜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导大多数被剥削、受压迫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应该明白我们在理论宣传文章和演说中不知疲倦地闸述的一般革命前景,与我们今天就能用来动员群众、让他们事实上与军事独裁制度对立的实际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分。国民会议口号就是这样的核心政治口号。”(托洛斯基给中国反对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意识水平尚未处于革命阶段,“真正民主议会”与“工人民主政权”的政治口号不仅没有对立,“在民主宣传及其鼓动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紧密的连接,并且这两方面的革命活动平行不悖”(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托洛斯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号召“不分阶级”的立宪会议,目的是揭露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拖延召开新议会的角色。在双重政权形成后的革命形势下,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今天我们在中港台直接号召苏维埃,不仅是冒险主义,更将自己排除在广大的民运群众之外的消极主义。
占领中环(香港民运议题的焦点)若果如目前一样,由资产阶级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领导,必定会妥协收场,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干预运动,提出工人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争取工人群众支持,挑战泛民领导。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随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条主义消极地与运动“保持距离”。我们绝不会犯上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