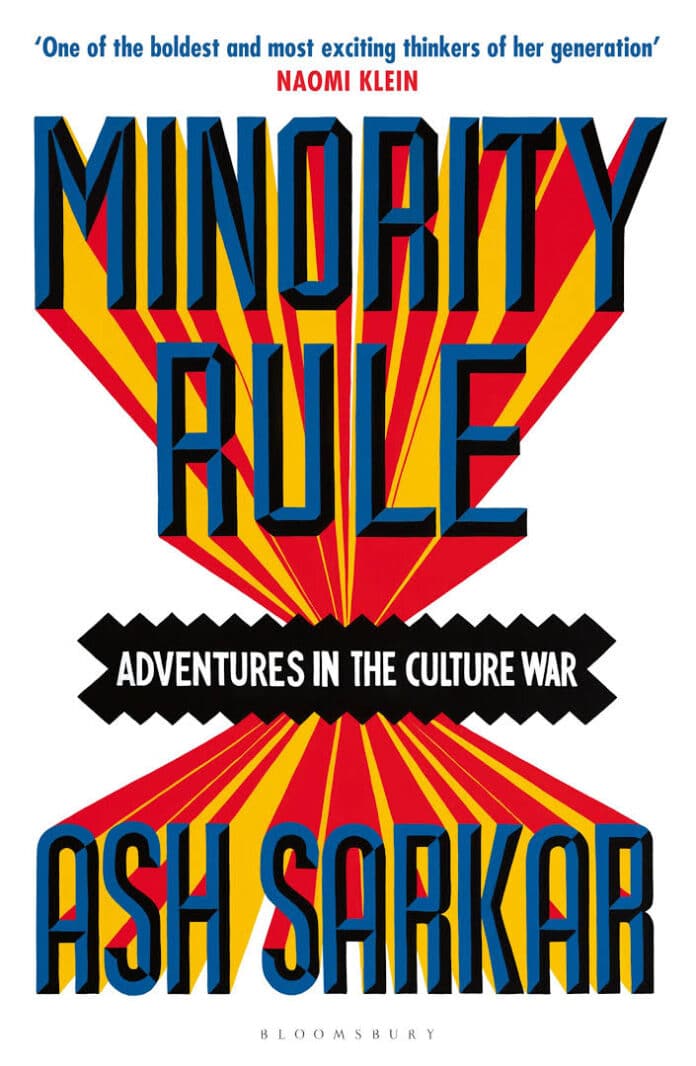这本书深入探讨日益两极化的公众辩论,而辩论的中心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相比起此书所撰写之时,对于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迫切。
Claire Laker-Mansfield 社会主义替代(ISA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少数派统治》一书中,诺瓦拉媒体(Novara Media)编辑阿什·萨卡(Ash Sarkar)探讨了已成为英国政治核心的“文化战争”。围绕身份问题的公众辩论日益两极化,而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书讨论了这种现象在媒体上如何呈现、谁从中受益,以及左翼政治在这种背景下的定位。
相比起此书所撰写之时,对于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迫切。这篇文章是在特朗普第二次掌权前写的——而特朗普的回潮对世界各地的右翼势力来说是一种鼓舞。2024年8月爆发的极右翼骚乱仅在后记中提及,而这篇后记也必然是在本书主题完成后写成。
身份政治的缺陷
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一开始并不是批判右翼所提倡的有害的、分化大众的政治,而是审视过去一段时间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政治思想与方法。第一章的题目是“‘我’如何控制了身份政治”。在书中,萨卡批评了主观性日益成为左翼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视角。她正确地指出,工人阶级遭遇的挫败、以及新自由主义成功削弱集体斗争组织,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背景。
她对主流形式的左翼身份政治的批评,未必新颖或具有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像萨卡这样杰出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身份政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圈子中的一员,但她却选择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些论点。她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解社会运作方式的最有用的框架,这一点也很重要。
《少数派统治》的开头章节很切实描绘道,以过度关注个人“生活经验”为特征的那种身份政治如何在左翼占据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思维方式,压迫性“制度”往往被视为数百万个个体权力差异与压迫性互动的累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了反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眼于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经济结构,然后研究这些经济结构如何产生、延续并通过不同形式的压迫来维持。
萨卡描述了对压迫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倾向于将焦点集中在人际互动的动态上,经常强调个人的表演姿态,而非集体的群众斗争,而这导致激进运动变得越来越无力,但这些激进运动却能对当权派构成挑战。她写道:“今天,身份政治的大多数表述都是混乱、分散且缺乏野心的。”这是一个简洁而准确的陈述。
她在整本书中采用的叙事方式倾向于轶事。这当然有其道理。尽管这本书并不总是拥有严谨的科学性,但它却使读者读起来轻松有趣。萨卡根据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左翼身份政治的主流形式如何使有益的讨论跑偏或偏离团结斗争。对于过去十年在英国活跃过的左翼来说,有一些故事听起来很熟悉——一场关于应对气候变迁的辩论因一名演讲者辱骂观众而被中止,网上的叫喊声迅速升级为社交媒体上的激烈攻击,等等。
萨卡指出,强调对不同受压迫群体经历进行分类与划分,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可简化的差异逻辑”。她批评了“盟友”这个模糊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令人困惑的劝诫,即要求个人“转移你的特权”到其他人,因为他们正经历你没有遭受过的压迫。她指出,这些想法具有足够的可塑性,以至于可以被世界上一些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机关拿来所用(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她惊人地回忆起特朗普时代之前“将CIA人性化”(Humans of CIA)广告宣传,该广告看起接受了“交叉性”。
理论
这种例子显然是荒谬的。但如果萨卡的论点有弱点的话,那就是她并未明确指出她所描述的那些理论观点本身存在的缺陷。她对于“交织性理论”、“特权理论”等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和滥用所进行的批判,确实一针见血。然而,这些术语所代表的理论本身,她基本上仍认为是合理的。
例如,在书的后面,她指出,认为“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放弃’‘白人特权’”,她准确地描述道这一种想法是荒谬的。她以工人阶级白人为例,他们可能在学校、照护系统中苦苦挣扎,或无法负担食物或能源。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人“转让特权”给任何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同时,萨卡也肯定了学者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的特权理论的基本有效性。
对于她所正确描述的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方法,与理论上支撑这些方法的因素,她在此未能将两者联系起来。她所批评的“利益冲突缘由”,是否在逻辑上没有联系到“赋予所有未经历过特定形式压迫的人‘特权’”的理论?事实上,依照这个定义,“特权”广泛适用于一系列负面因素 — — 不会面临种族歧视、不易遭受性别暴力、不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束缚等等。但这正好助长了萨卡所描述的,现代左翼身份政治普遍存在的那种“缺乏雄心壮志”现象。“教育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一项特权”这一口号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如果将没有遭受种族歧视视为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每个人都应享有这项权利,并且我们必须为之奋斗),那么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人们的眼界。从逻辑上讲,它强调的是个人,而忽略了集体的斗争和团结。
这并不是要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即那些没有经历过特定形式压迫的人在生活中具有相对优势。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压迫,会以人际关系中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应该对此提出挑战──既要在个人层面,也通过集体行动(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但萨卡的观点是正确的,她指出,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她所说的“预示性政治”——坚持认为政治组织团体必须先清除一切压迫性思想或行为的痕迹,然后才能开始努力为这个泡泡之外的世界的变革而奋斗。
事实上,在许多社运人士圈子里——特别是在那些与工作场所组织脱节最严重的圈子里——“做好分内工作”这一指示,很少涉及任何实际的组织工作。相反,这通常是呼吁自我反省与自我完善。这些本身并不是坏事。围绕压迫议题进行政治教育,是工人运动的重要且迫切的任务。挑战内部的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思想与行为,对于确保其团结至关重要。然而,过于严厉与不宽容的态度——特别是针对无意的微歧视(microaggression)、或明显因缺乏教育而造成的错误,也可能导致社运人士因反省而陷入瘫痪、甚至完全陷入不活动的状态。同样,提高我们自身的认识水平,本身并不会挑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维持压迫的庞大物质力量。
“受害者崇拜”
事实上,由于人们过度关注主观问题,以致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如何建构、以及为何会产生不平等和压迫等问题反而常常被推到次要地位。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萨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世界的最有用的思想体系。她将《共产党宣言》中“雄心勃勃”地号召建立“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与当今许多左翼组织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受害者崇拜”进行了对比。她将“受害者崇拜”描述为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暴力与压迫的生活经验成为赋予个人政治权力的一种筹码。
这本书准确地描述了竞争性受害者心态不仅存在于左翼政治中。萨卡称右翼存在着“多数派的身份政治”。她切实描绘了右翼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叙事,将边缘化少数群体描绘成与神秘的“精英”有联系,并密谋压迫多数群体。这打造了一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顺性别女性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跨性别女性,种族主义的真正受害者是白人,住房危机中的罪魁祸首是难民、而不是百万富翁房东们。
在一个有趣的章节中,萨卡叙述了本世纪围绕阶级的政治讨论的演变。特别的一点是,她详细描绘道,工人阶级从被说成无能的“低俗一族(chavs)”,到目前对所谓“白人工人阶级”大力推崇。在这种叙述中,“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观点,与所有其他工人的利益与观点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令人尴尬与震惊的是,她揭露了某些资产阶级评论人士(特别是德林波尔[James Delingpole]和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几乎在一夜之间,将白人工人阶级的描述从“粗野”改成“深沉、热情、爱国、且热爱民主的人”。
阶级斗争
描述这一过程的章节指出,2011年的骚乱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时刻。这些事件的起因是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达根(Mark Duggan)。骚乱始于托特纳姆(Tottenham),枪杀事件就发生在当地。但该次骚乱迅速传遍全国,各个种族背景的年轻人都参与其中。在此,她正确地指出,不同族群工人阶级青年所面临的一些相似的社会条件。这些无疑是造成这种普遍无组织的(并且在许多地方,具有很少政治意义的)愤怒爆发的核心原因。
但2011年也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有机会展现自己力量的一年,而这一点在书中全然被忽略。骚乱发生仅几个月后,就爆发了事实上的公共部门总罢工,展现了多元化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这场斗争的意义,以及它的失败(工会的右翼领导层造成的)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但这部分却在书中只字未提。如果英国工人阶级能够在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早期取得重大胜利,那么这或将有助于铲除分化工人阶级思想滋生的基础,正是这些分化思想使得工人阶级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相互对抗。
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也正是挑起“文化战争”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将社会的分裂引导到阶级以外的其他界线上,从而分化并削弱工人运动,并将对其制度所引发灾难性危机的责任转移开来。萨卡回顾了马克思提供的关于阶级的科学认识,尝试在现代背景下解释这一点,这样子的分析解释很有用处。她将此与资产阶级媒体常用的模糊的文化定义、或僵化的推销分类进行了对比。
《少数派统治》生动地描述了大量的“新闻业”如何堕落为大量生产诱饵式标题、从而助长文化战争叙事。社交媒体放大的是“热度而非亮度(译者注:即对于议题认识的清晰度)”。萨卡强调指出,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充当权威,而参与进入资产阶级媒体的商业模式。他们常常表现得好像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评论人士而非政治参与者一样——他们可以对最新的媒体“微事件”侃侃而谈,但却完全无法解决社会面临的大问题。
资本主义的反动转向
也许这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它有时过于注重表面内容。国际右翼势力的崛起,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深刻危机。这是统治阶级无法“用旧方式统治”的表现。
这与近年来全球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我们已经从一个时代过渡到了另一个时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以帝国主义冲突为特征的时期。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威权主义是这种转变的政治表现。面对危机,资产阶级为了自保,日益转向反动。“中间派”新自由主义政治人物所残存的社会基础,正迅速而急剧地瓦解。文化战争的诱饵式标题大军必然有助于强化这些进程。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
尽管有这样的弱点,《少数派统治》最终还是令人耳目一新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萨卡正确地指出:“我们所处的政治是社会阶级力量平衡的反映”。她指出了团结斗争的潜力:“当人们能够克服分歧,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一个向上的目标上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让那些囤积权力和财富的人害怕的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结尾。但特朗普2.0和英国右翼势力的崛起,特别是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使得这项呼吁变得更加迫切。正如萨卡所言,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围绕身份与压迫问题的斗争。事实上,这些斗争需要大力加强。但这确实意味着要以一种战斗的方式组织起来,建立团结。这意味着依靠我们身为工人的经济实力,采取统一行动,特别是罢工行动,来实现改变。在社会主义替代看来,这意味着要迫切争取一个新左翼政党,而这样一个政党要扎根于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者的鲜活斗争。这意味着为革命社会主义变革而斗争——而这只有在多种族、多性别的工人阶级的“巨大运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