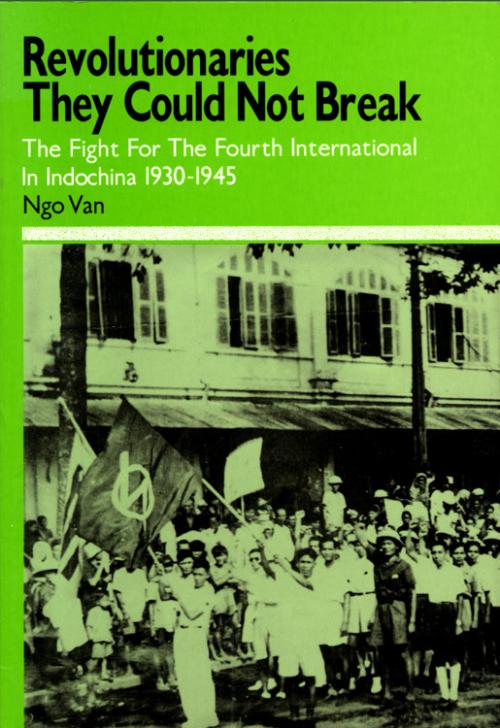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关于越南与法国殖民斗争的主流史观,往往反映了河内政权的斯大林主义陈见,对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拥护者的英勇献身不是无视就是诋毁。作为一位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吴文(Ngo Van,又名吴文雪Ngo Van Xuyet)将他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称)的经历撰写成书,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导正史观,是一本详实、励志,尽管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尾的历史纪录。
1930年代,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监禁,但他们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众基础,领导了好几次罢工并赢得多场地方选举。西贡有一条街道,曾经以一名被杀害的托派领导者谢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谢秋杜)命名,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赢得许多群众的支持。尽管1975年斯大林派统治了统一后的越南,将这条街名更名,但“西贡当地人仍然称其为『谢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当时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和共产党斯大林派领导的恶毒攻击。1945年,随着斯大林派巩固对独立运动的控制,数百位积极的托派被抹黑为“叛徒”或“法西斯间谍”而遭到屠杀,这让人联想到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二战后的第四国际领导出于错误立场,尾随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建国者)、毛泽东等斯大林主义领袖,也故意淡化了这些对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国际领导者帕勃罗(Michel Pablo)甚至告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与毛泽东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数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法国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为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国的)侨民之中招募而来。胡志明(又化名作阮爱国)就是这批早期生力军的一份子,他于1929年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PCI)的创党成员。与后来的托派们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在国外流亡。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发动的官僚主义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产主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甚至赞颂“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积极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不满该党领导庸俗的民族主义、以及斯大林渴望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的立场,因此走向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主张的国际主义思想与坚持阶级原则的政治路线。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随国民党的策略导致中国革命的血腥溃败之后,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亦想从反帝斗争中消除一切社会主义的内容,拒绝提出国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厂之类的要求,说这样会疏远本地还很弱小的资产阶级。后来,印支共产党甚至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还地于农民(土地改革),认为这会疏远越南的地主阶级。这种“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一在一个“最小公约数”的资产阶级纲领上。印支共产党一直坚持这种政策,以至于1941年,他们将自己化身成“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Vietminh),一个此前已经沉寂很久的民族主义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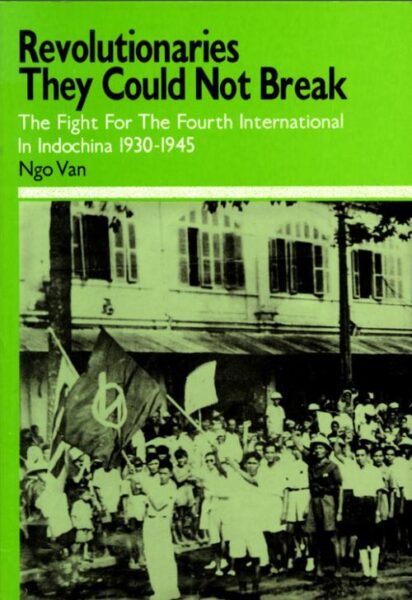
工人阶级和农民
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体现在两种不同的建党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组织规模尽管较小的城市工人阶级和苦力,特别是在西贡;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学生领导,并且倾向组织农民。
1930至1932年间,印支共产党领导了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和日薪劳工与法国当局不公正的人头税作斗争,但正如同吴文所指出的:“他们无法、也没有尝试在城市中发动运动响应。”
法国外籍兵团则以屠杀上万名农民作回应。尽管该运动的英勇,但印支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极左冒进错误。这发生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1928-34年),由于之前企图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机会主义政策失败,共产国际矫枉过正地要求每个地方都必须立刻“建立苏维埃”和“夺取政权”。
一旦农民运动平息下来,印支共产党便遭受无情的镇压,包括党总书记陈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产党支持者被控以“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当中8人被处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严酷劳役。
1931年11月,谢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对派。6个月后,他们开始发行双月刊的党报《无产》(Vo san)。1932年8月,《无产》的65名成员和支持者因从事“颠覆活动”被捕。印支共产党员的大规模审判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法国共产党斯大林派的党报《人道》(L’Humanité)却对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保持了冷酷的沉默。然而在西贡,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来,在市议会选举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知名民族主义者合组“工人名单”参选。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产党领导者被判处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单”中有2名候选人当选(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义者)。虽然市议会本身是一个无实权的机构,但这场选举在大规模镇压期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3个月后,法国殖民当局宣布这2位市议员当选无效!
联合阵线?
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贡进行了一段长时期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联合阵线是群众党派之间的务实协议,而不是小规模的宣传团体。列宁的建议是“分开游行,一同罢工”,意即行动统一,但政治旗帜要分明。
西贡托派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幸的是这点在吴文的书中并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选之后,谢秋收和左翼反对派领导扩大了与斯大林派的联盟,并同意联合发布周刊《斗争》(La Lutte)和联合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该允许的政治让步,同意“办一份捍卫工农的报刊,但限制不讨论涉及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
《斗争》报的机关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已经是个联合的党组织,且是个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联合阵线”。在1935年的市政选举中,4名《斗争》的候选人当选为西贡议员: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谢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吴文记录说:“4名『共产党人』在市议会中的充满力量的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民的热烈同情,并提高了群众的斗志。”但4个月后,这5个人因支持马车车伕的罢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们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对政治纲领和分析的妥协上,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与法国右翼共和党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面对这个震撼弹般的政治事件,《斗争》对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对1936年8月莫斯科大审判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也保持缄默。史实显示,当时托派领导认为国际问题可以与日常工作分开。他们并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审判的致命意义,了解到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义份子将把相同的做法引进到印度支那。这导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对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少数派于1935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布鲁姆(Le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当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布鲁姆政府没有放弃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体系”。正如吴文所说,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车中,“印支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斗争从纲领中抛弃,在公开言论中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法国帝国主义』”。
这种背叛为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迟至1936年12月,围绕《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开始抨击巴黎人民阵线政府未能解除对印度支那的镇压。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于是退出与托派的联合组织,宣称该组织已经“托洛茨基化”。这个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阶级中成长的转捩点。
受到法国工人的启发,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发了罢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业、煤矿、铁路和码头行业。正如吴文解释:“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自发的,然后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响下,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每天八小时工作、工会合法化、民主自由并终结暴政和罚金……”
这一运动导致法国当局作出了一些深远的让步,在交趾支那涌现的超过600个行动委员会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领导。
1937年2月,法国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记载:“支持第四国际的革命鼓动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贡提岸的工人阶级大众里,影响力不断增强。”同年7月,又再补充:“工人阶层中,托派政党比印支共产党拥有更多支持度。”
“保卫印度支那”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印支共产党领导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问题都应该从属于反抗“法西斯”日本的斗争。
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展开加速军事化的进程,为“保卫印度支那”而进行3千300万法属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战争举债,还试图征召2万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产党这时选择了支持法国政府。这两个议题都引爆了群众的烈火──反对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斗争,早已经历漫长痛苦的历史。
尽管如此,印支共产党还是呼吁人们自愿参军来支持“法国民主”。正如吴文所指出:“印支共产党的某些人对战争债券表现出极大热忱,甚至他们还提议将100元债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债券,好让穷人买得起。其他有些人则反对与殖民政权合作,却被革除党务……我们同志的声明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战争税、反对生活水平恶化。”
斯大林派被视作与法国当局及紧缩政策一伙,以至于当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钱的税时,工人就把这称作“第三国际的火柴盒”。
法国殖民地总督曾写道:“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相信……安南(越南)群众的利益驱促使他们靠近法国当局……而托派……则不怕推动当地人抗争,以便将可能爆发的战争变为他们的优势,以赢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产党的亲法立场,在1939年的市政选举中受到了惩罚。尽管托派遭到打压(所有会议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选入西贡议会,而斯大林派则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产党在组织方面受到打击的消息,传到仍在中国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对未来的可怕预言,他说:“面对托派分子,不能与之和解或让步。必须以各种方式揭露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敌意,一部份是由于胡志明希望与帝国主义达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此后共产党在法国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缔。在越南对于斯大林派与托派的镇压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被送进了集中营。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让印支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转,他们放弃了亲法的鼓动宣传,恢复了第三时期的“反帝国主义”策略。当日本于1940年9月在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登陆时,印支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冒进的、计划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国当局。和1930与1932年间的农民起义一样,这场起事也被残酷镇压。印支共产党的一次党内审判将这场灾难的责任归咎于2名地方党委书记,并将他们处死。
与此同时,日本与战时法国维希政权达成了协议,印度支那由日本军队占领,但继续由法国魁儡政权统治。胡志明在中国复活了民族主义的越盟,带领一支由500名越南侨民组成、在中日战争中由国民党训练出来的武装力量。正如吴文指出的那样,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种选边站的做法,一种寻求他国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国、俄国、美国、甚至法国);当中毫无无产阶级的立足之地。”
尽管胡志明采取左摇右摆的机会主义路线,但在日本战败造成的权力真空中,越盟却变成了越南独立斗争的领导。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苏联权威的强化,以及越南农民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但托派政党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犯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随着日本帝国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场革命浪潮。在秘密会谈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条件,让法国5至10年后才允许越南独立。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场,目的是要延长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战时同盟。
相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则呼吁展开大规模示威,并武装群众,以阻止法国殖民政权的回归。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鸿基(今下龙)、锦普地区,不受越盟控制的3万名煤矿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生产。他们控制了铁路和电报等公共设施,赶走了旧有的管理人员,并实行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资不论层级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个工人公社一直持续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团结”为名逮捕了矿工领袖,并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胡志明的军队甚至企图阻止农民接管土地,尽管最终他们被迫放弃。
交趾支那是越盟游击队进入的最后一个地区。但在这一带,尤其是在西贡的工人之间,托派有着巨大的权威。正如吴文指出的,“《斗争》的一伙人组织了大约1万8千名斗士和同情者。《争斗》(Tranh dau,《斗争》报La Lutte的越南语版)以日报形式复刊,印刷量超过1.5万份。”
1945年8月21日,西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有30万人参加,其中3万人跟随第四国际的旗帜,他们的口号是“武装人民”和“为工农政府而战”。
越盟到来
越盟完全没有参加8月21日的示威游行,反映出它在西贡缺乏基础。就在傍晚,越盟从周边的农村进入到城市里,并且绕过工人的控制,宣称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载着扩音器的厢型车巡绕着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这时越盟在西贡还不为人知,它在一份传单中自我介绍:
“越盟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与法国(?!)和日本战斗。我们是俄罗斯的朋友;中国与我们同心同德;美国梦想的是贸易而非征服;在英国,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倾向左派。谈判对我们来说将会很容易。”
斯大林主义份子一边兜售迅速而无痛击败法国的幻想,一边试图抹杀任何独立群众行动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员会。抵达西贡后,越盟在没有遭到日军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央邮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且呼吁在8月25日举行一次新的大规模示威,这次则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夺取西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权。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越盟支持者从周围的农村乘客车赶来。正如一位托派领导者所说,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背着人民进行的”。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斯大林派领导谴责“煽动者和挑衅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时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与托派打交道。因为托派主张民主的工农委员会和武装人民,在西贡人民中有着强烈的共鸣。
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
不幸的是,在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斗争》的领导又回到了10年前所谓“联合阵线”的错误立场,但是这次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开始群众还无法看透越盟的本质,一方面以华丽辞藻说“宁死也要独立”,实际上面对帝国主义、苏联官僚、国内地主与资本家的压力却不断倒退。当时根据群众的经验,如果得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的反对力量。数以百计的行动委员会已经出现,有可能成为西贡及其周边地区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但这需要一个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领导。
《斗争》的领导们一方面抗拒和较小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合作,但在总体方向上却想与越盟结盟,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斯大林派能够否决他们自己的行动。例如他们通过谈判之后,才组织一支隶属越盟指挥系统、被越盟“认可”的托派民兵。他们的越南语日报《争斗》当时看来已停刊。随着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谋杀),第四国际书记处犯下印度支那支部于1930年代同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本来已经政治混乱的印支托派在国际的错误领导下变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轻的前托派回忆道:
“我们的同志被自己的热忱和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冲昏头,忘记了堤防斯大林派。从那时起,我们的同志们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把工厂变成堡垒、准备内战的步伐。十月派(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激进分子只对《斗争》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评。”
在随后的事件中,这两个托洛茨基组织的民兵即使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仍毫无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装。他们或许是因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应,而拒绝了一个民族主义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农民追随,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压的目标。然而,托派只要能与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与之建立仅涉及自卫的务实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此时,谢秋收前往北部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或许是为了要和胡志明会面。过程中他被越盟逮捕并遭到枪决。斯大林派的私设法庭上,谢秋收令人动容的辩护,使得行刑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要由“检察官”从背后枪毙他。
西贡起义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国军队于同年11月重新占领印度支那这段期间,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将军率领一支小型的英国和印度部队进驻西贡。当他们到达越南时,他们发现西贡到处都飘扬著越盟的旗帜布条,上面写着“欢迎同盟国的到来”,还有四个同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新的越南国旗。格雷西后来回忆说:“我的抵达时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后我很快地把他们赶走。”
英军抵达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组织”的武装。打压托派的运动就此展开。一个斯大林派组织“解放旗”(Co giai phong)说到:“必须立即镇压托洛茨基主义的煽惑组织。”更宣称:
“……他们要求武装人民──这吓坏了英国来使。他们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给农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阵线并挑动地主反对革命。 ”
但是,随着英国人逐步打击越盟在西贡羽翼未丰的政权,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众压力下采取行动。9月17日,他们发起了罢工瘫痪西贡。9月21日,格雷西将军宣布戒严,禁止携带武器并查禁越南语报刊。英国士兵占领了西贡监狱,释放越盟关押的法国魁儡政权的俘虏,同时却把托派囚犯交给法国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国种族主义殖民者的向导下,英军从越盟手中夺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控制权,并触发翌日晚上的起义。西贡贫民窟和工人住区设置了街垒,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托派的民兵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战斗。数百名托派在战斗中阵亡。越盟此时却呼吁民众分散到农村并说“保持镇定,因为政府希望开始谈判。”然后,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也撤军到农村,抛弃了他们在西贡工人阶级之间的位置。实际上,这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解散。在农村,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大多数情况下还遭到越盟屠杀。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发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赛罗纳的事件,成为决定西班牙革命未来走向的关键转折。尽管西贡的托派在街垒和工人街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只满足于当越盟的左派批评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为西贡群众的新领导。
法国回朝
10月2日,法国政府与越盟西贡地区委员会达成了停战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斗争》组织领导者悉数被执行死刑,罪名是“让敌国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样,斯大林主义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对抗反动势力,而是打压革命左翼、打击所有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诉求的努力。
11月,当英国将西贡的控制权转让到法国手上,越盟再次放弃了这座城市。正如吴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运动已经溃散。托派大部份领袖被杀害。民族主义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镇压。这为法国帝国主义的回归开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纬16度线上一分为二,南部由法国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军的存在(首先是国民党军队然后是法军),同时又尝试与法国谈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国土,胡志明还是不放弃谈判!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后来之所以能从自己的政策的烂摊子中全身而退,是由于他们完全预料之外也未曾支持过的1949年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地震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政治成本 。
随着越南的历史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吴文的著作即时地填补了重要的历史缺页。尽管它没有彻底分析这一时期托派在政策和战略方面的错误,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在越南的卑劣影响,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诚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来争取独立,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