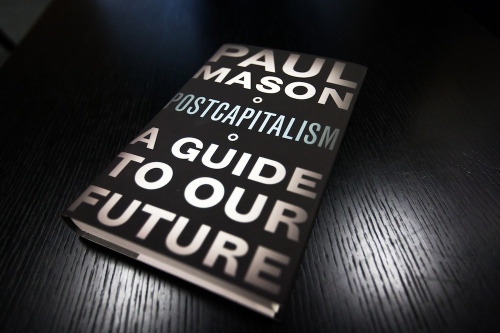书评:《后资本主义:通向未来之路》(保罗.梅森着)
彼得·塔夫(Peter Taaffe),社会主义党(CWI英格兰及威尔士)总书记
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最新著作《后资本主义》(Post Capitalism)为我们展现了新社会的图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的恐怖在书中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他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大众通过斗争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过时的旧思想。
书名:《后资本主义:通向未来之路》
作者:保罗·梅森着
发行:艾伦.雷恩出版社,2015年
《后资本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写的《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书评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4/11/03/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review-the-marginal-cost-soc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处。里夫金写道:“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终结……它渡过了鼎盛时期,开始缓慢地死亡”。梅森则写道:“资本主义的前途黯淡无光”,新自由主义时代最终是厄运。书本出众地描写了衰落的资本主义,值得一读。
梅森和里夫金两人都认为科技的巨大进步将埋葬资本主义,尤其资讯科技是无法限制在民族国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狭窄空间内的。资讯科技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令生产多每件产品的额外成本近乎为零,进而令商品价格降到零或近乎为零。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利润——资本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里夫金)。
里夫金埋头研究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如他所承认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出身背景。里夫金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验主义结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它为群众广泛拥护的时候。而且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里夫金的思想表明,我们有可能把一些作为个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运动这一边。
与里夫金不同,保罗.梅森则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从这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思想上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十分悲观,特别是提到他认为已经过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相反,他钟爱着“后资本主义”这一块政治上从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带。里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在与未来时,都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组织代替资本主义。梅森在书中写道:“我们看到了自发兴起的合作化生产……平行货币、时间银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间……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贷形式……我相信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传和保护”。
那么如何才能到达这个乐土?不是通过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梅森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而是通过“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会知识联系起来的每个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惠及所有人类”。由此可以看出,先后作为《新闻之夜》和《第4频道》记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领运动的影响。
占领运动无疑是美国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腊)新生代政治觉醒的重要阶段。我们欢迎这一进步。但是梅森学到的不是这场运动的优点和潜力,而是它的弱点:在对抗资本主义时所谓的“自发性”,因而还有它的幼稚性。事实已经证明,有意识的“去组织化”的泛青年运动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现代”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令国家机器转为中立。占领运动的一部分人士——例如从卡萨玛.斯旺特(Kshama Sawant)当选西雅图市议员这一事件中——很快学习到一点:政治运动对于实现运动目标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中,群众意识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这场运动曾在上一次大选中实际上抵制了“政治”,最终却导致右翼人民党(PP)获胜。因此群众开始意识到激进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并促成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西班牙语意为“我们可以”)的崛起。至于这场新运动能否有效驾驭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激进的不满情绪则是另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力量党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对所谓“种姓”(caste)的模糊批评——而不是明确批判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与组织——来建立一个“反政党的政党”,现阶段此种政策不可能争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会民主力量党在民意支持率的确出现下滑。
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梅森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合作创立者——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他批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他们领导的俄国革命。他也高度批评对一战前经济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一战爆发只是因为“错误的末日预感”。另外,他还推崇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后者在一战前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支持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辩护士。
梅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的观点是错误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耗尽其所有潜力之前都不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过我们不能以肤浅的经济“决定论”来理解这句话,不幸的是,梅森就是这样做的。经济发展具有最终决定性,但是国家与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仅有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变动与政治变动之间辩证关系——原因可以成为结果,结果也可以成为原因。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对二战后革命浪潮的背叛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和1950-75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于同一原因,我们反对从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里借用的长波理论,或者叫做超级周期理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对此做过评论。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钵的梅森等人所设想的50年周期。他们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线性经济进程,而没有充分考虑国内外巨大政治变革的影响。
梅森也没忘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他在参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个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裂出来的小型政治团体)时曾追随过托派。他所攻击的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1946年提出的一个错误的经济分析。那时战斗派(Militant,英国社会主义党)的先驱者考虑到了政治变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党人和斯大林派对战后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据这些因素,战斗派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因而成功地预见到1945年工党政府能够实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梅森犯了类似的错误。列宁、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战前为回应改良主义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经为战争本身所证实。他们承认在战争爆发前资本主义是相对进步的,能够推动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劳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这并不是说如果革命在19世纪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业和社会就不会以快得多的速度发展。
然而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前行,同时也令无产阶级——它未来的掘墓人——不断壮大。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限,从对生产的相对阻碍变成了绝对束缚,民族国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产力的喉咙。战争是无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在一战前的繁荣期——大概从1896年到1914年——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有所缓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适应了这种局面。工人阶级因此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准备。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战争中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的背叛行径完全令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迷失方向。
三年的残酷战争为革命——特别是1917年俄国革命——铺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却写道:“法西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毁灭是组织化工人200年来的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具有决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这200年里——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类历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俄国革命,而不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们只是减慢了社会和工人运动的前进步伐。
为拯救资本主义而奋斗?
这些并非只具有历史价值的抽象问题。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说一些让左翼感到痛苦的话:马克思主义误解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往在人类社会中最像一个进步的、集体的历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的头脑充斥着“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着推翻这个制度……左翼著作中到处散布着为200年失败史开脱的借口:国家太强大、领导太软弱、工人贵族的影响力太大……工人阶级远不是社会主义的无意识的承担者,他们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用行动表达出来。他们想要一个能让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资本主义……这并不是思想落后的结果,而是一种公开的战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这种战略的基础:存留在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技术、个人自主和社会地位。”
所以,不时发生战争、经济和社会浩劫、革命和起义的20世纪并非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无产阶级建立“可生存的资本主义”的尝试。梅森竭力否定俄国革命、1918-23年德国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静坐罢工和1930年代美国与革命潜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当时本可以发动十场革命。
更不用说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罢工和群众占领工厂的运动,还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革命剧变。让我们回忆一下,1975年斯皮诺拉(Spinola)政变失败后,《泰晤士报》宣称“葡萄牙资本主义已死”,因为在起义工人的压力下,银行被收归国有,70%的工业由国家接管。这些看来都是因为误解!群众抛洒热血、做出巨大的牺牲与努力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建立另一种资本主义。
梅森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断言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改头换面的工人阶级;而是网络化的人类”。就这样,工人阶级一下子消失了。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新意。他只是复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别是那些在苏东剧变后从斯大林主义倒向欧洲共产主义的人,他们为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领导英国工党向右转提供了理论依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书中得到赞扬。他认为去工业化宣告了工人阶级的死亡。
尽管发达工业国家的传统产业工人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其数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大规模工业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们明白现在传统产业已经进一步削弱,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受雇于运输业、工业等行业。从最近伦敦地铁工人的一系列罢工中可以看出,他们能够而且也将发挥关键作用。
即便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的“特权”阶层正在无产化。教师、公务员、邮政工人和大学讲师的工资经常少得可怜。他们视自己为无产阶级、加入工会并采取其他行动。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大型运动,以及英国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时10英镑的运动。我们还看到呼叫中心员工和亚马逊员工反抗日益严苛的工作条件。他们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工人阶级普遍情绪的影响,不仅在行业层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
社会主义意识
广泛的社会主义意识尚未出现,即便在希腊也是如此,尽管经济深陷危机,引发了空前的阶级愤怒和阶级行动。英勇的工人阶级发动30多场大罢工,确实痛击了希腊资本主义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众掀起巨大的社会浪潮,英国则出现了科尔宾(Corbyn)现象。这些都是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着贝利雅派和资产阶级。
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释这些斗争为何还没令工人阶级取得成功的时候,梅森认为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对于群众意识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决定论的。群众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具体事件、工人阶级——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的集体经验,以及党和领袖的关键的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其19世纪鼎盛时期——例如德国——直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20世纪头十年它对成千上万的工人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这帮助数百万人树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并将之与日常经验相结合。演讲、新闻报章和宣传册等各种宣传手段令资本主义的问题家传户晓。
罗马神话说密涅瓦(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脑袋里出来时就身披甲胄、手执金矛。显然梅森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无需客观条件的变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样凭空出现。他在《卫报》写道书本的概要:“过去25年间,左翼的方案失败了。市场摧毁了计划;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世界劳动力极大扩展,他们看似是‘无产阶级’,但他们根本不像以前那样思考和行动”。这些话说明他还没有明白,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观念造成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存在。
即便庞大的官僚集团带来沉重负担,计划经济仍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参照点。它的瓦解让统治阶级有机会大规模鼓吹资本主义相对“声名狼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败退——群众意识倒退了——即便其严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后对工人运动的打击。
2007/08年危机后,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渠道反覆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市场”是无可替代的。工会领导和社会民主党人则附和这种论调,越来越向右翼倾斜。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大众及其先进阶层不断投身于反抗资本冲击的斗争之中,却仍未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真正能替代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
不过,卡萨玛.斯旺特(Kshama Sawant)当选西雅图市议员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竞选美国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已经表明,在犁过的地上,社会主义意识的新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连美国——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无法避开这一趋势。被危机撕裂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会落后太多。
空想社会主义
梅森用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没有丝毫新意,它并非对“过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据他自己所说,其本质上是借由合作社回归到协作理念。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运动出现之前,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旧思想而已。欧文是一个拥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区让我们初步了解了社会主义可能带来什么。不过,这只是乌托邦,他的方案最终未能成功。在资本主义的海洋中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小岛,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其目的是“在社会的背后改造社会”。
梅森声称,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物质匮乏,但现在资讯科技的应用和分享行为等诸多因素已经使物质资料大大丰富了,所以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他在许多方面都犯了错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提出此种方案,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独立力量。不过他们在宪章运动——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实现了这一点。
在大概十年的时间里,宪章运动经历了阶级斗争的所有阶段,从和平请愿到革命总罢工。当时24岁的恩格斯在他那本杰出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这段经历,而梅森则对这段经历加以攻击。他同样攻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1848-51年革命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繁荣期并造成英国工人运动出现一段“温和期”所做的解释。
梅森写道:“恩格斯说工人变得温和是因为他们分享了英国帝国主义力量所带来的好处。不只是熟练工人——他把他们描述成‘工人贵族’——而且还有广大群众,恩格斯认为大英帝国扩张导致的价格下降使他们得益。但是,他认为英国的竞争优势是暂时的,熟练工人的特权也是暂时的”。
恩格斯说对了。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失去它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了工人阶级,导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码头工人等奋起反抗。当然,熟练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们也受到英国资本主义衰落的影响。梅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作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的分析是错误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观点禁不起认真检验。他用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拼凑出一堆经济和政治的大杂烩,以配合他那乌托邦式的观点。
在其结论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认:“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他已经用自己的简要模型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模型丝毫不能说明今后一段时期内英国和全球的动态。我们从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乌托邦主义者是后资本主义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一切先驱者”。这里丝毫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和即将战斗的工人阶级。
很明显,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失败对梅森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对此做过细致的电视报道。希腊、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将从这一段惨痛经历中学到很多。我们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还需要能和群众一起抗争到底、铲除资本主义、开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领导者。不幸的是,保罗·梅森的书对培养这样的领导者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