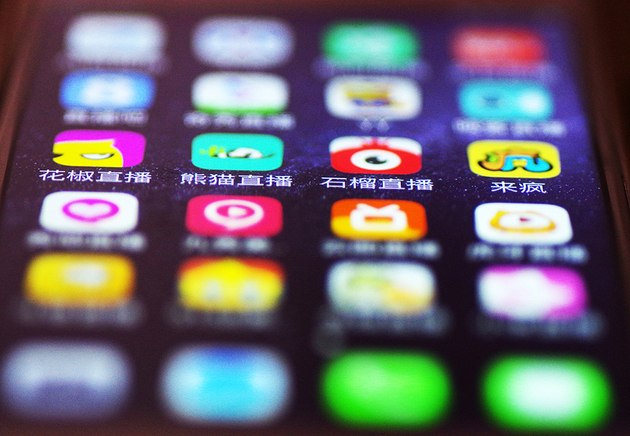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猹 中国劳工论坛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一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仿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主播从业者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一般人印象里,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一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里,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一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一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一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一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台会对主播进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台斗鱼为例,一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着,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着便是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一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路平台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制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制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路平台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制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一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复。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制创作自由。社会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审查扼杀创作力
此外,我们反对一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台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